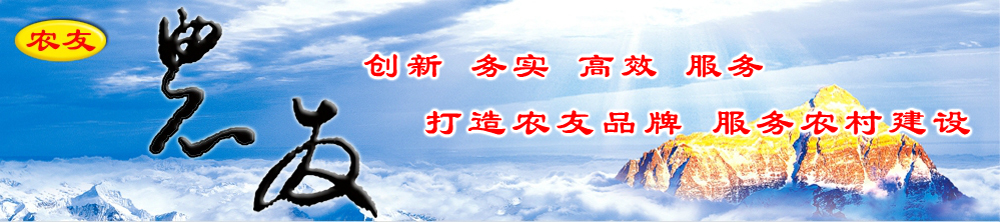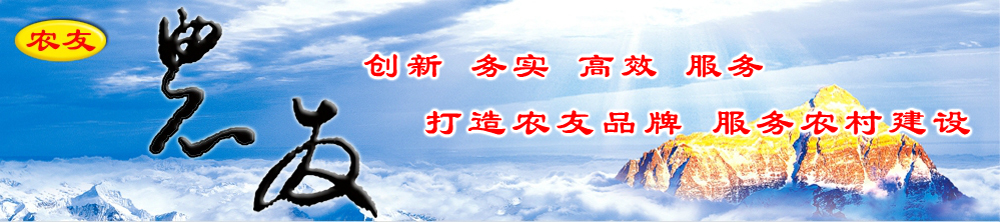在山西省阳高县兴苑村,村民正在村里新建的新农网络之家上网,每个电脑跟前都座无虚席。虽然已是中午时分,但似乎没有人有离开的意思。如今到新农网络之家上网已成为这个村村民最大的娱乐活动。党支部书记冯瑞逢人便讲述信息生活给整个村庄带来的改变。兴苑村今年的西红柿全部通过网络交易销售了出去,仅此一项,就增加了40多万元的收入。
在我国,像兴苑村这样的网络之家还有4个。从2006年开始,中国扶贫开发协会中国村络工程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信息扶贫”:免费捐赠电脑,并建立一个适合他们的网络平台。这样的“信息扶贫”还在继续,越来越多的村庄将会感受独特的信息时代。
村民呼唤“鼠标种田
网络备耕”的时代
“鼠标种田、网络备耕”这句话缘自山西应县龙泉村党支部书记刘建银,如今在中国村络工程办公室里成了一句名言。宣传事务处处长张一星喜欢讲这样一个故事,2003年刘建银到县城一位朋友家做客时,偶然从网上看到一条胡萝卜种子信息,经联系很快引进了两个新品种。然而,尽管当年的胡萝卜取得了丰收,但因为信息不畅,2000多亩胡萝卜还是有一大半烂在了地里。刘建银开始打起网络的主意,2004年,龙泉村率先开通了“龙泉在线”网站,迈出了网上查询、网上交易的关键一步。刘建银还把手机号码放在网上,用上了QQ等即时通讯工具。生意从此接踵而来,龙泉村也成了网络上远近闻名的“中国胡萝卜第一村”。
“龙泉村代表着千千万万个渴望信息致富的村庄。我国越来越多的实际情况表明,在近年来的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特别在中国信息化综合水平蒸蒸日上的同时,各地的信息化水平差距正在拉大,尤其是城乡之间,一条无形的‘鸿沟’开始形成。我国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生活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在信息与网络革命中与发达地区的距离越来越大,信息贫困已经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林嘉騋说。尽管近年来国家在缩小数字鸿沟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城乡数字鸿沟仍然呈现扩大的趋势,原因之一是互联网在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和普及速度缓慢。为了在新形势下开展好扶贫开发工作,中国村络工程选择了以乡村社区为扶助对象,以信息化为手段,依靠城市大众的关爱,整合丰富的信息资源,为乡村社区带去多元化的公共福利以及大量的发展机遇,将为广大农村建设出一个又一个充满活力的“数字化细胞”,从而为农村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一公里的障碍
“我们的信息扶贫并不是简单地捐助电脑,而是要真正地突破农村信息最后一公里的障碍。”林嘉騋告诉记者。
在通讯行业里,“最后一公里”通常指的是从用户驻地业务集中点到用户终端之间的传输及线路等相关设施,是通信公司把线路铺到社区后,由社区入户的那段距离。也就是说,“最后一公里”实施的顺利与否,是整个社区接受信息的关键。在所有“最后一公里”中,“农村”这个大的社区因为基础硬件设施落后,人均收入太低以及文化产业发展的滞后成了最长和最难走的“最后一公里”。突破这最后一公里,也成为信息扶贫的关键所在。在中国村络工程成立之初,就把建立有效机制彻底解决最后一公里难题作为工程的主要目标。那么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的障碍究竟在哪呢?
村络工程把最后一公里的障碍分解为五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网络服务、网络接入、上网终端、信息转化和上网需求。这其中,前两个障碍靠资金投入能部分解决,但是最后三步才是困扰农村信息化的根本难题。
“另外,很多农村信息化工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单一的部门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例如,中国移动主要大力解决网络接入问题,而上网需求等问题则更多的需要教育等部门来努力,所以,整个农村信息网络工程的顺利实施应该是多方通力合作的结果。”林嘉騋表示。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经过大量的研究工作,中国村络工程解决农村“最后一公里”的方案新鲜出炉。概括地讲,就是“靠中间、抓两头”。靠中间就是依托和利用国家基础网络,抓两头则是指“上头和下头”。“上头”指中国村络工程大力整合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种信息,如农业大学、清华大学的远程教育,各种农业市场行情信息等等,把这些内容变成农民会用、好用、爱用、常用的信息,下头指的是村络工程在行政村建立免费向农民开放的网络应用中心,把服务放在农民身边。
于是,在行政村100多平米的房间内,有了新农网络之家。据不完全统计,新农网络之家共包含远程教育、学历教育、社会捐赠、扶贫跟踪、农资产品订购、技能培训、务工信息、小额贷款等30多项功能。
谈及新农网络之家是如何在如此狭小的空间内实现那么多的功能时,林嘉騋说:“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兼容并包,让大家联合起来为农村服务。清华大学的远程教育内容丰富、技术成熟,中国村络工程架上卫星接收器,就可以让村民们获得来自中国著名学府的教学服务 |